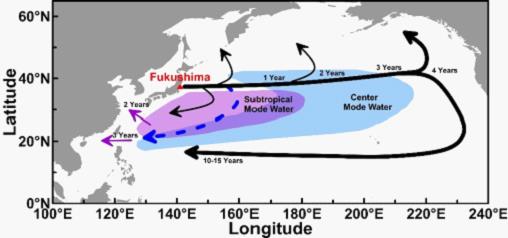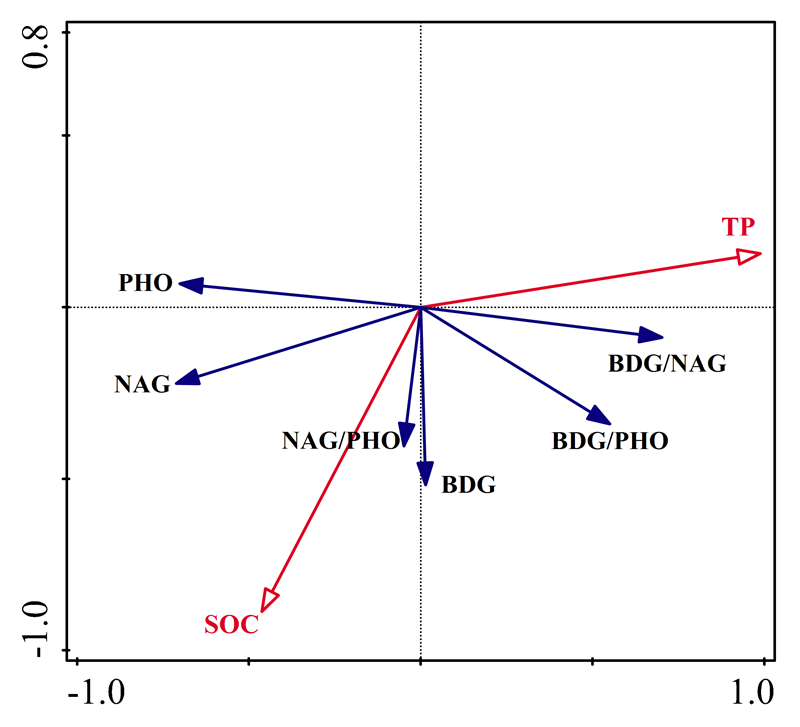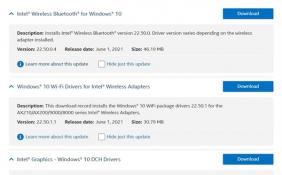舉國體制建平臺 強“芯”之路沒有“個人英雄”
盡管江蘇長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電科技)在集成電路封裝測試擁有全球第三、中國第一的市場份額,但在其技術副總郭洪巖看來,其發展仍面臨著諸多難題,比如技術產品更新迭代慢、人才缺乏、產業鏈聚集效應不足。
事實上,這并非長電科技一家的困惑,而是整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值得欣慰的是,解決這些挑戰逐漸有了思路。比如,浙江省正在打造集成電路“萬畝千億”新產業平臺,實現政產學研業的深度融合。
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陳左寧在近日召開的“2021中國(紹興)集成電路產業創新發展學術峰會”上所指出的,“集成電路產業沒有‘個人英雄’,需要在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上的各個環節協同配合、形成合力,把產業整體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到更高水平”。
合作開放是關鍵
“隨著外部環境出現更多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全球集成電路供應鏈正加速重構,呈現出本地化、多元化的布局,我國集成電路挑戰與機遇并存。”陳左寧表示。
集成電路行業包括設計、制造、封測、裝備與材料等環節,任何一個環節的獨自強大,都不能建成“芯片強國”。
中國工程院院士吳漢明指出,由于中國集成電路產業起步較晚,而國際早期布局的企業形成了較多的知識產權保護,給國內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因此,未來集成電路領域是整個產業鏈的競爭和對抗,而不是點的競爭。”
當前,我國芯片制造產能正加速擴大。但吳漢明并不認同“產能過剩”的說法,“真正的芯片需求非常大,只要有理性、科學的安排,產能、創新發展空間很大”。
過去50年,“摩爾定律”支撐著集成電路行業的發展,即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集成在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每隔18至24個月將增加一倍,計算成本呈指數型下降。但隨著工藝器件,以及種種物理化學性質走向極限,“摩爾定律”逐漸終結已成為行業共識。
如何在“后摩爾時代”乘勝追擊,是企業界和學界面臨的重要課題。
“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未來發展需要開放、合作,在‘十四五’期間,國內集成電路行業有望打通設計、制造、封測、裝備與材料等環節,迎來新的發展。”陳左寧說。
舉國體制建平臺
全產業鏈集成,需要政產學研等多方聯合。“集成電路產學研依然是‘兩張皮’。”吳漢明直言。
在吳漢明看來,其實產學研的分工很明確,產業技術就是企業來做,產前技術是學校跟進,而從產前技術到產業技術,產學研的重合領域是最需要關注,也最有發揮空間的,這需要創新平臺支撐。
“該平臺有3個特點,設備和制造一體化、新工科模式、做成套工藝的驗證。這樣既可以大幅提高學生培養質量,又能降低企業創新風險。”吳漢明說。
浙江大學教授嚴曉浪也表示,構建“芯片—軟件—整機—系統—信息服務”產業鏈,應從國家層面進行戰略布局,推動成立行業領域性的芯機聯動,以整機企業提供優秀解決方案為導向,以創新模式開展高校、科研院所與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的多層次技術交流和合作,以創新技術、產品設計、解決方案和成果產業全鏈條實現領域內的新型技術轉移轉化。“企業的需求一定要成為芯片設計的對象,在產品定義和設計上,整機企業要有很大的發言權。”
嚴曉浪還提到,要建立自主知識產權的推廣平臺,產業化基地在產業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抓住后摩爾時代迎頭趕上的機遇,加速新型舉國體制下的公共技術研發平臺建設,由單點突破轉向產業鏈集成,夯實發展基礎,打通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全鏈條’。”陳左寧說。
人工智能尋突破
我國集成電路行業處在重要機遇期,如何尋找新突破、開創新局面?
清華大學教授魏少軍表示,集成電路的出現和計算緊密相連,計算正走向多臺機器對多臺機器的泛在計算。從能源與公用事業、制造,到公共安全、通信等,5G和人工智能應用推動集成電路進入社會各個角落,集成電路技術也迎來重大變革。
隨著半導體技術飛速發展,單個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高速增長。“微納系統集成、芯片架構創新,以及新器件新材料和新工藝3個領域的創新,將是集成電路跨過5納米需攻克的幾個關鍵技術。”魏少軍說。
針對計算芯片設計面臨的性能、功耗、靈活性相互制約的固有矛盾,魏少軍提出了軟件定義芯片技術。近年來,魏少軍團隊研發了Thinker系列人工智能芯片,其硬件功能能夠隨著軟件功能的變化實時變化,適應不同神經網絡,具備高計算效率、高能量效率以及高靈活性。
魏少軍認為,當前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核心受制于人,產品處在中低端”的情況還未徹底改變,基礎研究和基礎人才沒有跟上需求發展是重要原因。他建議建立涵蓋行業五大板塊的創新體系、理清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的學科體系和知識體系,未來大有作為。(韓揚眉)
責任編輯:hnmd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