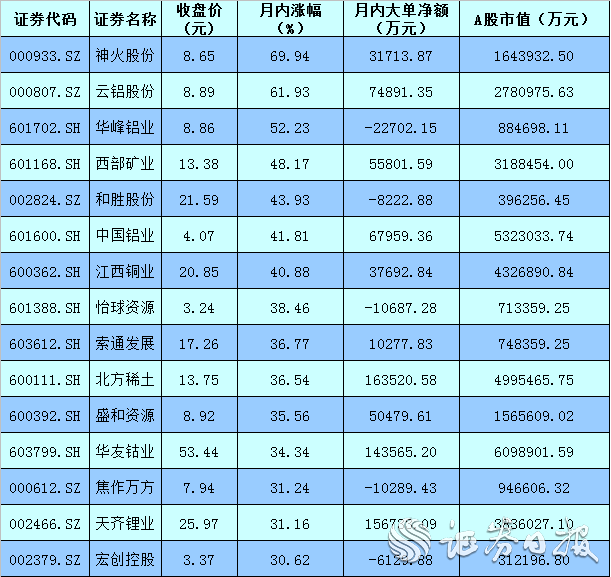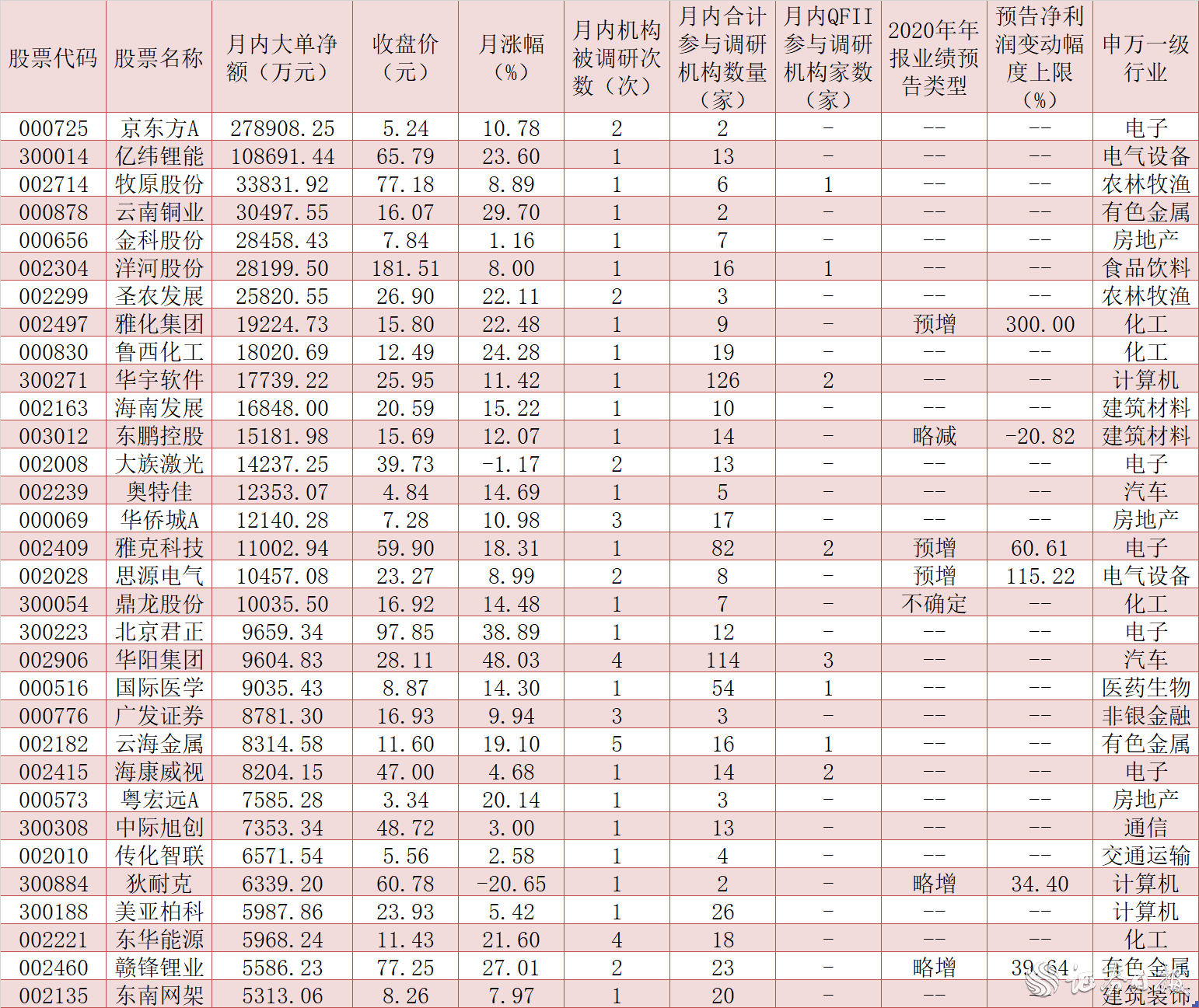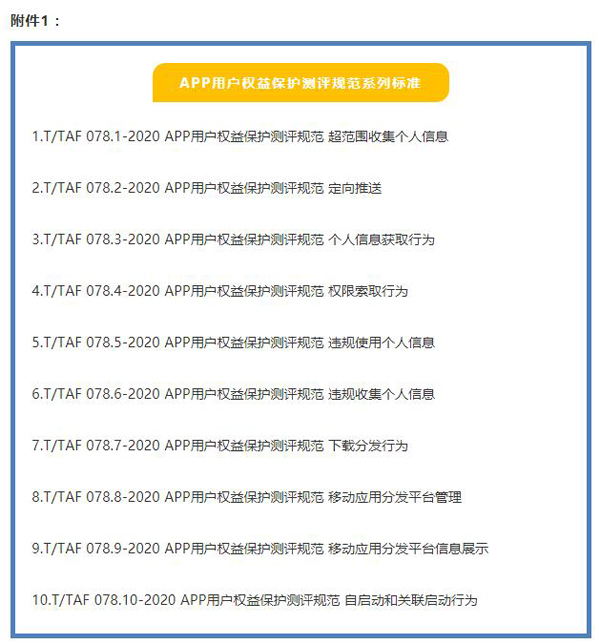永煤債違約事件持續發酵 中國境內百萬億債市違約處置問題成關注焦點
中國境內債券市場規模巨大,已經逼近100萬億元。隨著近幾年中國債券市場的逐步開放,國際投資者的持有規模在不斷上升,但占比仍然不高,且主要集中在利率債。隨著中國債市的開放步伐加速,國際投資者對于境內信用債市場的關注度提升,而違約處置問題也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
“永煤債違約一事才真正令市場感覺到了違約處置的重要性,因為感到痛的機構比較多,包括銀行。光靠廣義基金的力量很難推動改革,必須要有銀行的參與。”某國際大型資管機構債券基金經理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標普全球評級近期特別發布了《中國企業違約后何時該期待何事》。標普中國企業信用研究首席分析師張積豪對記者表示,在鼓勵境外投資者進入境內投資的“債券通”開放三年之后,國際投資者對信用債的參與率仍有待提升,部分原因正在于違約后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不盡人意的處置結果——追償程序漫長,且充滿變數。提高違約處置的透明度,可以增強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券市場的信心。
積極的趨勢在于,越來越多的國企采用較為清晰的法庭內處置路徑,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民營企業也建立了違約處置范本,會提高違約處置的可預見性。隨著案件數量的積累,境內外市場的具體處置方法都有可能得到進一步完善。
國企法庭內處置案例漸成樣本
今年的債市違約案例不斷發生,讓市場各方參與主體認識到,中國亟待完善債券重組、處置、追償機制。中國的《企業破產法》1986 年試行,1991年擴大實施,2006年修訂,到今年對于國際投資者來說,也體會到了它的重要性。張積豪說,這是因為幾個標志性的美元債違約案起到了推動作用,債務人和投資人逐漸明白,法庭處置可能好過法庭外一拖就是數年的妥協過程。隨著中國債券市場已經完全打破剛兌,預計相關案例也會越來越多。

有的外資機構認為,一些國企違約后的處置方式上正在起到示范作用。2020年2月,方正集團被法院裁定進入重整程序;沒過幾個月,又有幾家備受關注的違約國企相繼被提起訴訟,如青海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和天津物產。
一般來說,在違約發生后,債權人向地方法院申請對債務人的資產進行凍結。例如,永泰能源在違約后1天資產便被凍結,北大方正則用了4天,中民投用了1個月。
“相比國企,早前民企更多采取庭外和解的方式,但其中銀行成為主要受益人,而其他廣義基金投資者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證,處置周期往往長達兩三年。例如中民投、永泰能源等在違約后兩年也沒有看到任何司法程序的進展,國企在這方面反而處置效率更佳。”張積豪稱。
一直以來,銀行之所以沒有動力推動庭內處置,也是因為銀行和廣義基金的利益訴求并不一致。“銀行在意的是給企業續貸、獲得利息,但廣義基金需要應對贖回需求,因此看中的是本金的到期償付。”前述債券投資經理對記者表示。
“尤其是銀行是企業資金往來、投融資活動接觸最多的金融機構,企業和銀行通過存款、票據、貸款、授信等業務深度合作,且銀行營業網點眾多,可較為全面、超前監測到企業的現金流情況。但非銀機構在上述方面能力較弱,因此在企業出現現金流壓力或信用風險時,反應不如銀行快。”天風證券副總裁、天風國際證券董事局主席翟晨曦對記者表示。
在海外市場,這種利益訴求不一致的情況同樣存在,但上述投資經理表示,關鍵在于有沒有特定的法律條款來對發行人的行為和違約處置進行約束,一般國際市場都有限制性條款來保護廣義基金的權益。
那些可待完善的地方
一些投資機構對中國境內債券市場的違約處置程序還有一些疑問,認為可以進一步完善。
首先,多數違約案例仍采取庭外處置的方式。一般債權人大會都在違約后的三周至三個月進行,會議的目的主要是聚集債權人來達成協議,也有會議的目的旨在提示投資者發行人無力償付本金,或尋求延期支付本息。對此,有的投資人的疑惑在于,在庭外處置的過程中,銀行和其他債券投資人幾乎都是分頭會面,并沒有將彼此的需求相互進行協調。也正如上文所述,兩方的利益本來可能就是不一致的,一方得到的結果往往對于另一方是負面的。
當前企業違約后,債委會主要由銀行牽頭,但信用債的投資者眾多。翟晨曦稱,單一投資人出于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可能屏蔽債券管理人或債券主承銷商及其他債券持有人,私下和發行人進行協商。尤其是持券比例較高的債權人,可能談判到比較有利的處置措施,如單獨的資產抵押質押、場外兌付等。但是,非銀機構話語權較弱,在違約債券的處置過程中常常處于不利地位。
其次,張積豪表示,很多機構完全是突然違約,毫無任何先兆。例如北大方正在違約前兩周還發行了15.5億元的債券,而青海省投資集團則在違約前的兩個季度還發行了3億美元的債券。此次永煤控股在違約前也發行了中票,同時管理層進行的一系列資產重組似乎是在試圖提振市場信心。張積豪說,這種行為的確看似在給予投資人信心,但其實傳遞出來的信號完全是誤導性的。
此外,中國境內市場對于違約的語言定義還有一些模糊。標普認為,海外對于未按時還本付息的債券就定義為違約,但中國境內則會使用“延期償付”等語言。“隨之而來的違約是真實的。例如,媒體此前報道稱,天津物產正在和債權人討論將短期債券(1年以下)延期,但3個月以后,它就直接違約了。”張積豪說,還有這樣的情況,國企發行人往往會出現在到期前大幅折價回購的行為(distressed tenders)來降低其債務負擔,但這種行為通常是在債券第一次違約前的幾個月出現,有時甚至是違約后的幾個月(例如天津物產)。此時,債券的折價幅度往往很深,尤其是在債券違約后,但這往往只反映了在流動性和市場信心極差時的債券交易情況,而并未真實反應發行人的償付能力,這無疑極大地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
不過,標普也認為,隨著違約案件數量的積累,境內外市場的具體處置方法都有可能得到進一步完善。若能增強投資者信心并增強中國債券市場的流動性,那么對發行人也會是好事。(周艾琳)
責任編輯:hnmd003